新書推介 | 通向現代選舉之路
無論是現代選舉原生模式還是次生模式,在選舉制度逐步展開的過程中,都需要處理現代選舉內在要求的普遍、平等、直接、自由、定期選舉的原則,並設立以理性和效率為原則的選舉管理機構。
從18世紀開始,為什麼現代國家的選舉制度從歐洲發軔之後,世界各國的選舉制度在從隱到顯或從無到有的變遷過程中,經歷的是不同的道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不久,伴隨着一系列新興獨立國家的出現,就已經有學者開始比較系統地思考這一基本問題。在比較政治學領域興起的政治發展研究中,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曾經佔有相當的篇幅。20世紀70年代以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出現之後,這一問題再次引發了不少新的研究興趣,新的理論模式更是層出不窮。
本文摘選何俊志教授新作《通向現代選舉之路》(香港三聯書店2022年9月出版)中有關理解現代選舉制度的差異化道路的論述,回顧前人對於選舉變遷的研究歷史,探討現代國家走向選舉制度的多樣道路。
01
反思現有研究
如果我們立足於選舉制度的研究來反思現有研究,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當代政治學的主流理論在處理選舉制度的變遷時,並沒有將選舉制度的變遷作為一個獨立的因變量,而是將其作為作為代議民主制度的一個測量指標來加以處理。
自熊彼得(Joseph Alois Schumpeter)開始通過選舉競爭來作為經驗民主的標準,達爾(Robert Alan Dahl)進一步將其作為最低意義上的民主測量標準以來,當代世界的主流數據庫和現實民主研究的專著,鮮有不將選舉制度、尤其是自由和包容的選舉作為民主的測量標準。我們在理論分類部分所提到的達爾的分析框架,在測量民主與非民主及民主化的動態過程時,只不過是將選舉的包容性(普遍性原則)和競爭性(自由化)原則作為兩項尺度。這一做法實際上代表了當代政治學民主化及選舉研究的主流途徑。在“沒有自由的選舉就沒有真正的民主”這一原則指導之下,選舉制度只不過是當代主流政治學者觀察和測量民主及其動態過程的一項經驗指標。在那本影響廣泛的著作中,亨廷頓(Samuel Philips Huntington)雖然對民主的定義保持了一定的謹慎態度,但是討論的過程中還是直接斷定:不民主的國家沒有選舉上的競爭和普遍的參與。
戴蒙德(Larry Jay Diamond)早就指出,這種直接用選舉制度來定義民主的兩大危害在於:過分強調選舉的競爭性而忽略了民主的其他維度;把決策權的重要領域置於由選舉產生的官員控制之外。這種將選舉作為測量民主的標準的做法在後來的研究中所面臨的一個非常尷尬的問題就在於,相當一部分學者都承認,20世紀後期出現了一種難以定義的政體,即“選舉威權政體”或“競爭性威權政體”。選舉威權政體或競爭性威權政體在選舉方面的特徵高度接近競爭和參與的標準,但是其實際權力的行使又不符合民主的基本要義。一些學者認為,僅僅在1990-1995年期間,全世界就有35個國家可以納入競爭性威權政體的範圍。在當代政治學的政體分類中,只好將這類政體納入混合政體的範圍。蒂利(Charles Tilly)也曾經指出,這種將選舉與民主做直接捆綁的做法,要麼是一種程序視角,要麼則是一種過程視角,其結果都是從選舉的角度來定義民主。將“選舉民主”等同於民主的做法,會導致在利用這些標準來判斷一些國家的政體性質時出現混亂,例如是否要將哈薩克斯坦和牙買加的政治制度納入民主政體的範圍時,可能會出現不同的結果,並且會忽視民主的本質。
這種將選舉制度僅僅處理為政體層面上的民主與非民主區分標準的做法,不但已經引出了新的政體分類的難度,而且也在相當程度上忽視了選舉制度的相對獨立性。在將選舉制度完全作為一個概念的特徵或者測量指標時,對選舉制度自身的獨立屬性就難以觀察到。結合選舉和民主政體的變遷歷程就可以看出,在歷史上,只有在19世紀晚期之後,選舉制度才開始作為民主政體的支撐性制度;即使在今天,選舉制度與民主政體之間也並不一定有一一對應的關係。因此,如果我們要考察選舉制度本身的變遷規律時,不能簡單將其作為民主政體的構成要素或者測量指標來加以對待。
與在政體研究中僅僅將選舉制度作為一個測量指標而處於依附地位相反的一種現象是,在政體研究的下一個層次上,比較政治學研究的主流理論在研究現代政黨體系的變遷時,又將選舉制度作為自變量加以處理,主要研究不同的選舉制度對政黨體系所產生的影響。在這一傳統中,選舉制度又被當成一個完全獨立的變量,研究的重點則集中於既定的選舉制度對特定國家的政黨體系、政治穩定的公共政策的影響。自迪韋爾熱(Maurice Duverger)提出有關選舉制度與政黨體系之間基本關係體現為選舉制度對政黨體系的決定性影響作用之後,比較選舉制度和比較政黨研究的學者圍繞着這一現象已經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傳統。在這個傳統中,大多數學者都肯定了選舉制度與政黨體系間的“迪韋爾熱定律”的有效性,並且重點考察的選舉制度的政治後果。
這一研究傳統顯然有其明顯的合理性,因為在可以觀察和測量的範圍內,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一個國家或地區的選舉制度都處於相對穩定的狀態,而政黨體系、政治穩定和公共政策都有可能因為每一次具體的選舉而發生或大或小的變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集中考察選舉制度的政治後果的相關著作,是在20世紀60年代之後才逐漸成長起來的一個領域。正是因為20世紀60年代之後多數歐美國家的選舉制度都處於穩定狀態之際,才可以比較集中地考察選舉制度的政治後果。
如果將英國國會從14世紀開始嘗試國會議員直接選舉視為現代選舉的早期開端,並且將國會議員的直接選舉作為通向現代選舉的第一種類型,首先需要明確的兩項基本前提是,古代的選舉在歐洲地方層面的延續和國家層面上的議會制度的逐步成型。長期延續的地方選舉為國家層面的選舉提供了制度供給的基本形態,現代議會制度的成長則在國家層面上提出了選舉的需求。
因此,一個國家現代選舉制度出現之前是否存在議會,就是決定現代選舉制度變遷模式的第一個決定性變量。在那些已經有議會存在的國家中,現代選舉制度的發展過程,實際上就是一個選舉產生的議員逐步替代世襲、任命或當然產生的議員的過程。在這些國家中,首先出現的是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逐步替代通過其他途徑產生的議員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首先出現的是直接選舉。伴隨着直接選舉的議員規模的逐步擴大,競爭性的因素不斷增加。選舉競爭的過程如果能夠得到規範,則自由化的成分增加,並通過自由競爭不斷動員大眾捲入選舉過程,從而帶來包容化和平等化;如果競爭過程沒有得到規範,則將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維持寡頭競爭的模式,直至再民主化過程才開啟包容化和平等化。顯然,作為原生型的代表,英國的現代選舉制度的變遷模式,就屬這種類型中的典型代表。
如果在現代選舉制度啟動之前沒有成熟的議會制度,或者是經過革命和重大改革摧毀了傳統的制度體系之後,新建立的議會制度需要選舉之時,由於在短時間內要選舉產生大量的議員,在選民幾乎完全沒有受過選舉訓練的情況下,絕大多數國家都會在直接選舉與間接選舉之間進行某種組合。美國的道路是眾議院直接選舉、參議院間接選舉;法國和德國的道路是先間接選舉,再直接選舉;日本是在經過反覆權衡之後採用直接選舉;墨西哥則在一段時間內搖擺於間接選舉與直接選舉之間。
此後出現的第三種類型絕大多數是以蘇聯為模版。在這種類型的選舉制度變遷過程中,由於社會主義革命開闢了更多的選舉職位,同時是以先鋒隊政黨動員直接動員社會底層捲入選舉過程,平衡數量龐大的選舉職位和選民群體的中介力量就是先鋒隊政黨。選舉過程本身就是一個政治啟蒙的過程,按照列寧設計的選舉模式,在社會底層的文化基礎薄弱的背景下,只能在一開始採用間接選舉的方式進行選舉。隨後的改革道路,主要是依據經濟社會的發展和文化水平的不斷提升之後,再逐步提出直接選舉的層次,並根據政治發展的階段而增加競爭性的因素。
最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擺脫殖民地地位而獨立的國家或此後才開啟選舉的地區中,普遍、平等、直接和自由選舉的原則已經作為現代選舉的基本原則而確立,尤其是平等和普遍原則已經被廣泛接受。所以,在這一時期進入選舉的國家和地區,更容易一步到位同時採用直接、普遍、平等和自由選舉並行的方式。
因此,就選舉制度的歷史變遷過程而言,在現代選舉開啟之前就已經有議會的國家,如果沒有經歷過重大的革命和急進改革,則更有可能出現由直接選舉帶動自由化選舉,再由自由化選舉帶動普遍性選舉和平等性選舉的道路。在那些經歷過重大革命和改革的國家中,則更有可能先經歷一段時間的間接選舉之後,再過渡到直接選舉,然後才會逐漸走向由直接選舉帶動的自由化選舉的道路。而一旦普遍化選舉的原則得以在世界範圍內確立之後,普遍選舉的原則也就更多地在一些國家的選舉開啟之間就直接採用。簡言之,本書總結出的通向現代選舉基礎道路的三個基本變量是:先前是否存在成熟的議會制度、是否經歷過重大革命和改革、選舉制度的開啟時間是在普遍選舉原則確立之前還是之後。第一個變量決定了一個國家的選舉制度先以直接選舉起步;第二個變量決定了一個國家的選舉制度先以間接選舉起步;第三個變量決定是一個國家的選舉是否在起步環節納入普遍性原則。
如果我們充分認識到現代各國選舉制度變遷過程中的這種選舉制度的內生性問題,就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在選舉制度的變遷過程中,一個國家或地區的選舉制度起步模式已經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這個國家或地區的選舉制度變遷的道路。在逐步落實現代選舉所要求的直接選舉、自由選舉、普遍選舉和平等選舉原則的過程中,如果在起步階段已經落實了一個基本原則,在下一階段的任務就是落實另外一些原則;一些國家先採用某一原則,另外一些國家先落實另外一些原則。但是,除了直接選舉原則之後,自由選舉、普遍選舉和平等選舉原則的落實都沒有終點。
要處理選舉制度的內生性問題,還必須要面對的一個問題就是選舉制度與政黨體系的關係。如果說在現代選舉制度出現之前有沒有成熟的議會制度構成了現代選舉制度的變遷是否更有可能以直接選舉起步和漸進改革的方式進行,現代政黨與選舉制度的關係則對選舉制度的具體類型的分佈起着更為直接的作用。
早在1958年,就已經有研究者提出,至少從比利時、丹麥、瑞典、挪威和瑞士的選舉制度變遷過程中可以看出,這些國家之所以將決定選舉競爭模式的多數決制改為比例代表制,是因為在多數決制與多黨共存的情況下,由於選舉與議席之間的關係嚴重扭曲,現存的政黨為了維持在將來選舉中的存活,才共同決定將競爭規則由多數決制改為比例代表制。因此,在這些國家所經歷的選舉制度與政黨體系的關係,是先前的政黨體系在決定後來的選舉制度,而不是像迪韋爾熱定律所宣稱的那樣是選舉制度在決定政黨體系。與此類似的是,羅坎和李普塞特(Arend Lijphart)等人也認為,歐洲大陸國家之所以在20世紀20年代普遍採用比例代表制來替代多數決制,主要的原因在於先前存在的大黨擔心在選舉權普及之後,新興的小黨會危及到傳統大黨的生存。
晚近的研究則發現,在19世紀中期之前,絕大多數國家的議會選舉制度都屬複數選區多數決制的選舉制度,即在一個選區內不止產生一名代表,決選規則為多數決制。先前存在的政黨為了應對普選時代的來臨,大致分化成了三種不同的改革類型。第一種類型是在保留多數決制規則的同時,將選區規模收縮為每個選區只產生一名代表。第二種類型是在保留大選區的同時只維持絕對多數規則。第三種類型是在保留大選區制的同時採用新的比例代表制。雖然出現了這三種類型的差異,但都是為了在選舉過程中不讓某一政黨能夠贏得全部席位,以適應普選之後的多元化社會的需求。
顯然,在上述國家中,政黨對選舉制度的改革主要圍繞着選舉競爭規則而展開,改革的前提是政黨已經內化於議會制度之內。但是,在社會主義革命之後,由於領導革命的先鋒隊政黨在革命成功之後再創立新的代表機構,故無論是代議機構的組織模式還是選舉模式,都需要服務先鋒隊政黨的執政需求。與此同時,先鋒隊政黨在創立了新的選舉制度和代議體系之後,並沒有完全進入代議機構之內,而是在代議機構之外領導着新創立的代議機構和選舉制度。先鋒隊政黨除了通過新建立的選舉制度和代議體系來建立合法性之外,還在代議機構和選舉制度之外另有合法性的基礎和動員民眾的通道。在代議機構和選舉制度之外,除了革命所帶來的合法性之外,還通過績效建立合法性,而且還可以通過執政黨自己的通道在選舉之外直接動員民眾參與現代化建設。因此,與前期政黨和非殖民化之後出現的政黨不同的是,在革命過程中產生出的先鋒隊政黨,在革命之後構築了兩套合法性體系,即選舉的合法性和績效的合法性,而且在選舉之外另行建立了一套直接動員民眾的動員體系。在隨後的改革歷程中,執政黨對選舉制度的設計模式,就在更大程度上取決於選舉制度的運行在整個執政體系中的地位。無論是在革命還是建設過程中,執政黨的工作模式都是在各個時期內先確立中心工作,然後再根據選舉制度在中心工作中的地位來決定選舉制度的改革進程和方式。
綜合前述的結論可以看出,當代世界的選舉制度的原型,是中世紀與君主制共存的議會邁向了選舉。在自由和平等原則逐漸普及到現代政治之中後,君主和貴族退出了政治舞台,人民主權原則逐漸通過主要以代議民主的方式落實。在落實代議民主制的過程中,普遍選舉原則才成為一項重要的標準。因此,如果要考察現代選舉制度的基本類型,第一種類型就應該是與君主制共存的選舉制度。在君主和貴族退出之後,在落實普遍選舉原則的過程中才逐漸產生出現代意義上的政黨。從而與君主制共存的選舉制度就過渡為與現代政黨制度共存的選舉制度。只不過,由於時代背景的變化,現代政黨制度在各國的產生模式不一樣,所以與政黨制度共存的選舉制度又可以分與一黨執政共存的選舉制度、與多黨競爭相結合的選舉制度(又可以細分為多黨競爭和一黨獨大)和一些國家和地區採用的非政黨型選舉制度。
進一步總結此書可以還可以發現,在作為原型的與君主制共存的選舉制度向與政黨制度共存的選舉制度過渡的過程中,前述的第一種類型更容易導向多黨競爭的選舉制度;第二種類型則容易經歷曲折、並且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經歷一黨獨大;第三種類型則更容易走向與一黨執政共存的選舉制度;第四種類型則多屬二戰後的非殖化政權,因此具體類型比較多元化。
本文選自何俊志著《通向現代選舉之路》第十一章〈理解現代選舉制度的差異化道路〉,原文注釋從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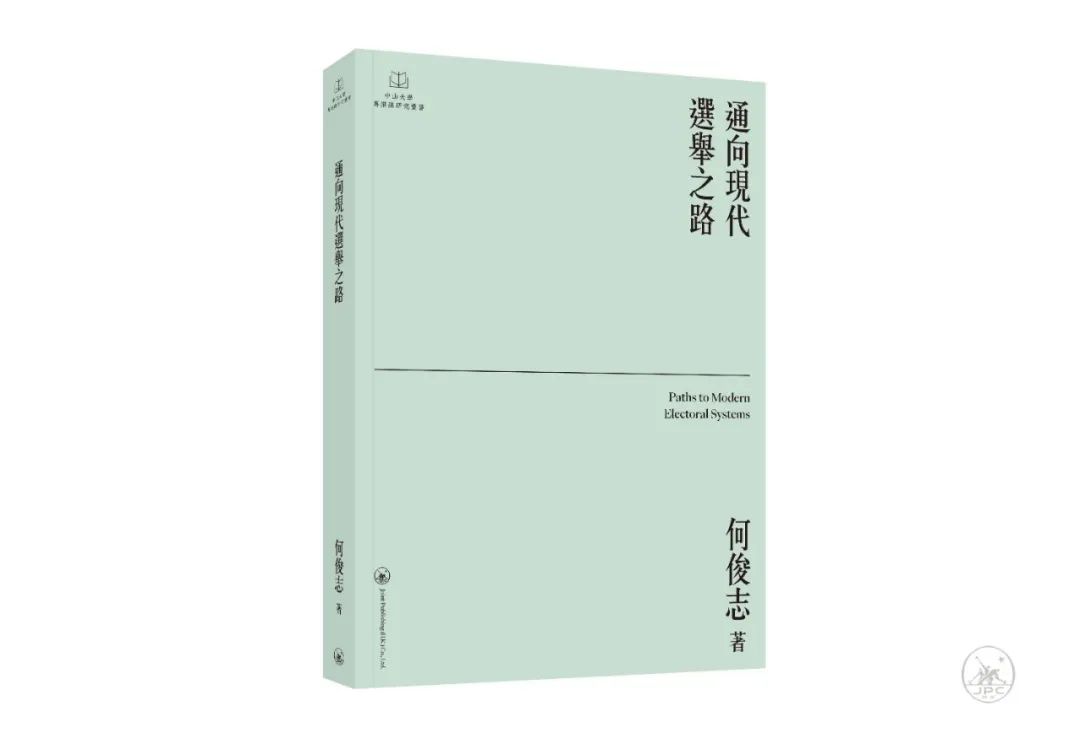
點擊封面直接購買
《通向現代選舉之路》
Paths to Modern Electoral Systems
叢書系列:中山大學粵港澳研究叢書
作者:何俊志
ISBN:9789620450532
2022年9月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何俊志,1973年出生於四川省平昌縣,2003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政治學理論專業,獲法學博士學位,曾經在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學院和哈佛燕京學社從事訪問研究,現為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教授、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院長,主要研究方向為比較議會與選舉制度,出版專著包括《制度等待利益》、《選舉政治學》和《從蘇維埃到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等。


